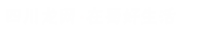6 [转载]一份值得感动的爱情——山楂树之恋
2010年08月05日穿了套洗褪了色的军衣军裤,很精悍的样子 。他们两个站在河沿措辞,长林不时指指校门方向,两个人你杵我一拳、我杵你一拳地讲笑,大概长林在讲他的犯险记 。然后老三朝校门方向望过来,吓得静秋一躲,以为他看见了她 。但他没有,只站那里看了一会儿,就跟长林往渡口方向走去了 。她也跟了出去,远远看他们两个 。她看见老三像小孩同样,放着大路不走,走在河岸边水泥砌出来挡水的“埂”上 。那“埂”只有四寸来宽,老三走着走着,就落空了均衡,吓得她几乎叫作声来,怕他顺着河坡滚到水里去了 。但他伸开手,身体摇晃几下,又找回均衡,接续在“埂”上走,像在走均衡木同样,而且走得飞快 。她很想把他们俩叫住说几句话,但既然老三躲着不见她,她就不善意思那样做了 。看来他真的跟长芳说的那样,是个心肠很软的人,见不得别人受苦,以是他帮大秀,帮她,现在又帮长林 。今天的车票必然他买的,他肯定知道长林找不到路,以是一直陪着长林到校门口 。她想老三必然把她让给长林了,或他本来就没打她主意 。但她不愿意信赖这一点,他那时不是很“争嘴”的吗?总在跟长林比来比去,怎么一下就酿成长林的“导演+向导”了呢?书里写的“纨绔”公子都是要“据有”了他的猎物才会收手的,难道他已把她“据有”了?她恨死了那些写得模模糊糊的书,只说个“兽性大发,据有了她”,但又不说到底怎么样才算“据有”了 。可是她隐隐地觉得“据有”之后,女的是会怀孕的,《白毛女》里面的喜儿不就是那样的吗?样板戏《白毛女》把这点删掉了,但她看过娃娃书,知道是有这一段的 。老三抱她还是上半年的事,她的“老朋友”已来过好多回了,应该是没怀孕吧?那就不算被他“据有”了吧? 她想起放在长林包里的钱,怕他傻乎乎地弄丢了,或让他妈洗掉了,就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走到渡口 。当他们坐的渡船离了岸的时候,她才从岸上大声喊长林:“长林,我放了二十块钱在你包里,别让你妈洗掉了 。” 她喊了两遍,预计长林听见了,因为长林在解捆包的绳索 。她看见老三扭头对划船的人措辞,然后俄然从座位上站起来,从长林手里拿过包,就往船头走,把船搞得乱晃 。她怕老三要还钱给她,吓得转身就跑 。跑了一会儿,她才想起他是在船上,能把她怎么样?她放慢脚步,想看个究竟,刚一转身,就看见老三向她跑过来 。他的军裤一直到大腿那里,全都湿淋淋的,贴在身上 。她惊呆了,已十月底了,他不冷吗? 他几步跑上来,把那二十块钱塞到她手里,说:“你把这钱拿着吧,冰糖是别人送的,不要钱的 。你用这钱买运动服吧,不是要打角逐吗?” 她完全僵住了,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她需要运动服打角逐 。他仓促说:“长林还在船上,现在肯定慌了神了,他不知道路——我走了,晚了赶不上车了 。”说完,他就返身向渡口跑去了 。她想叫住他,但叫不出口,就像她每次在梦里梦见他时同样,说不出话,也不会动,就知道望着他,看他越走越远 。那天回到学校,她底子没心思打球了,老想着他穿着湿淋淋的裤子,要好几个钟头才气回到家换掉,他会不会冻病?他怎么恁地傻,就从船上跳到水里去了呢?他不会等船划到对岸,再坐船过来? 后来有好多天,她都忘不了他穿着湿裤子向她跑来的情景,她觉得他不应该叫“纨绔”公子,应该叫“湿裤”公子 。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他怎么知道她打角逐需要运动服? 去年打角逐他们排球队没穿运动服,因为K市八中地处小河南面,相当于郊区,很多学生都是菜农的孩子,经济上不宽裕 。角逐前,教练勉力鼓吹过,说每1个人都要买运动服,但队员们都很抵制,就没买成 。他们那次就是穿平时的服装去赛球 。熬头场角逐的时候,一演员出场,刚喊完了“友谊熬头,角逐第二”,裁判就叫两边队员背对裁判,记载每1个人的球衣号码和站位 。他们演员出场的六个队员全都傻了眼,因为他们服装上没号码 。裁判把教诲局主管角逐的人找来了,说:“这群丫头既不穿球衣,又没号码,怎么角逐?” 教诲局的人把教练万教员叫到一边儿,语重心长地教导说:“你身为教练,难道不知道排球角逐站位很重要?六个队员的位置是轮流转的,后排不能在前排跳跃前动作扣球 。有的队只有1个主攻,如果都像你们这样不穿带号码的球衣,那他们的主攻从后排跑到前排去跳跃前动作扣球,裁判怎么看得出来?看不出来,怎么判人家犯规?” 熬头场还没打,裁判就判他们输了 。万教员低三下四地恳求,又做声泪俱下状,把队员们的贫穷掉队描述了一通,教诲局的人才赞成他们接续角逐,但迫令他们用粉笔把号码大大地写在服装上,否则不让他们到场角逐 。后来的几场角逐,都是一演员出场就被对方球队和看客猛笑一通,说他们是“杂牌儿军”、“乡下妹子” 。八中球队被这样挖苦,战斗意志一蹶不振,打了个倒数第三归来了 。但万教员死也不平输,说如果不是因为球衣闹恁地个不愉快,八中女队肯定能步入前六名 。以是万教员就逼着队员们买球衣,叫各人把钱交了,把尺码说了,他统一去买,省得每1个人自己去买又买得花花绿绿的纷歧致,还是被人笑话为“杂牌儿军” 。这回万教员很强硬:“你们不买服装,就不要打球了 。” 队员们一听就慌了,都把钱带来交了 。可静秋其实是没这笔闲钱,而且乒乓球队那边也要买运动衣,她想把两边的教练说服了,让他们决定买同一种颜色同1个式样的,那她就能够只买一件 。但两个队要求是纷歧样的 。排球角逐是在室外,下次角逐时间比力冷,教练说要买长袖的,保暖,而且有长袖护着,接球的时候手臂不疼 。乒乓球角逐是在室内,以是教练要买短袖的,说你们穿得“长落落”的,怎么打角逐?不光要买短袖,还要配一条运动短裤 。排球队万教员催了一阵,钱收得差不多了,就拿去买了运动服,印了号码 。平时跟兄弟学校排球队打友情比赛的时候就叫队员们把运动衣穿上,气壮如牛,先声夺人 。静秋没买运动服,万教员知道她家比力困难,就安慰说:“不打紧,不打紧,演员出场的时候我叫替补队员把服装借给你穿 。” 可替补队员不能演员出场已经是憋了一肚子火了,现在还要把球衣借给别人穿,更是一百个不耐心 。静秋也不善意思穿别人的服装去赛球,就勉力推脱,说我就坐旁边看 。但她是球队的二传,是主心骨,哪能不演员出场呢?以是教练每次都逼着1个替补队员把服装借给静秋,搞得那人不舒服,静秋也很难堪,有时碰到打角逐就干脆告假不去 。她不知道老三怎么知道这些事的,难道他认识球队的教练或球队的某个队员?或他时常在啥子地方看她打角逐?但她起根没在角逐时看见过他,难道他真是侦察兵身世?可以暗中察看她而不被她发现? 她决定从这二十块钱中抽出一些去买运动服,因为老三冒着严寒跳到水里把钱送给她,不就是为了她能买运动服吗?她买了,就遂了他的意,如果他能在啥子地方看见她穿运动服打球,那他一定很开心 。万幸万幸,两个队的队服除了袖管长度纷歧样,颜色和式样都是同样的,可能那年代也就那么几个样子 。她买了一件长袖的运动服和一条短的运动裤,准备赛排球的时候就穿长袖的,赛乒乓球的时候就把袖管剪下来酿成个短袖,比及赛排球的时候再缝上去酿成长袖,反正她针线活好,缝上去也没几多人看得出来,只要没人扯她的衣袖,想必不会穿帮 。球衣号码可以自己选,只如果别人没选的都行,她看了一下,三号还没被挑选出的人掉,她马上选了三号 。印号码要好几毛钱,她不忍放弃,就自己用白布剪了个号码缝在球衣上了,还照别人球衣剪了“K市八中”字样,缝在球衣胸前,看上去跟别的队员的球衣别无二致 。十二月份儿打角逐的时候,静秋老指望老三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赛场,那样他就能看见她穿着运动服了 。但她没看见老三,后来她也很庆幸老三没去,因为那次K市八中女排只打进了前六名 。各人都说我们输球完全是因为我们穷,平时用橡玩具练习,可到了角逐的时候用的是规范球,是皮子做的,重多了,各人不习气,连球都发不过,教练你要逼着学校去买些规范球给我们练 。万教员说:“我保证让学校去买规范球,不过你们也要好好练习,否则有了规范球也是白搭 。” 于是球队加了很多练球时间 。静秋很喜欢打球,但她也很担忧,因为每次打完球就很饿,就要吃很多饭,高中生每月只有三十一斤粮,她妹妹也在吃长饭,哥哥有时从乡下归来也要食饭,家里的粮越来越不够了 。转眼到了1975年,1个春寒料峭的早晨,静秋跟排球队的人在操场上练球 。排球类场地离学校后门很近,不远方就是学校的院墙,只一人多高,排球经例会被打出去 。院墙外面就是农业社的菜蔬田,球一打出去就要赶快去捡归来,因为现在球队用的是规范球,皮子做的,如果被田里的水打湿了就会断线裂缝,搞不好还被路过的人捡跑了 。可是校门离排球类场地还有一点路程,如果从校门跑出去就太远太慢了 。排球队怕丢球,以是每次球被打出去,队里就会有人翻墙出去捡球 。不过不是每1个人都能徒手翻墙的,只有静秋和别的两个女人可以不要人顶就爬上墙头,跳到院墙外,捡了球又翻归来 。以是一有球打出去,就有人叫这几个人的名字,催他们快去翻墙捡球 。此日早上,静秋正在练球,不知是谁把1个排球打到院墙外去了,刚好她离院墙近,就听好几个人在叫:“静秋,静秋,球打出去了!” 静秋就“噌噌噌”跑到院墙边,单脚一蹬、两手一抓就上了墙 。她迈过一条腿,骑在院墙上,方将把另一条腿也迈过墙顶跳下去,就见一名活雷锋帮助把球捡了,拿在手里,准备向院墙内扔去 。那人一抬头看见了她,叫道:“小心,别跳!” 20 静秋也看清了那人,是老三,穿着一件军大衣,不是草绿色的,而是带黄色的那种,是她最喜欢的军色,以前只看见地区歌舞团的人穿过 。老三黑黑的头发衬在棕色的大衣毛领上,颈子那里是明净耀眼的衬衣领 。静秋觉得头发晕,眼发花,不知道是打球打饿了还是被老三的英俊照昏了,她差点从墙上掉下去 。他手里拿着那个排球,球已被田里的露水搞湿了一些,他脚上的皮鞋也沾了田里的泥土 。他走到她跟前,把球递给她,说:“跳下去的时候把稳 。” 静秋接了球,一扬手扔进校内,自己仍坐在院墙上,问:“你——怎么跑这搭来了?” 他仰脸看着她,带点歉意地笑着:“路过这搭,我这就走 。” 院墙内那些人在急不成耐地叫:“静秋,坐那里乘凉啊?等着你发球呢!” 她急急地对他说声“那我打球去了!”就跳进校园内,跑回自己的位置上去打球 。但她越打越心不在焉,老在想他恁地早路过这搭要到哪儿去?她俄然想起,去年的今天,是她到西村坪去的日子,也就是说,是她和老三熬头次见面的日子 。难道他也记得这个日子,今天专门来看她的?她被自己这个古怪的想法缠绕住了,老想证实一下 。她只想现在谁又把球打出去,她就能够翻过墙去,看看他走了没有,或问问他到哪儿去 。但这时仿佛各人都约好了同样,谁也没把球打出去 。她又等了一会儿,眼看练球就快结束了,她再不能等了,就借发球的机会把1个排球打到院墙外去,引来队友一阵不满和惊讶 。她不管别人怎么想,飞快地冲到院墙边,“嗖”地爬上去,二话不说就跳到对面去了 。她捡了球,但没看见老三 。她把球扔进校内,没有翻墙归去,而是顺着院墙往校门那里走,想看看老三有没有躲在哪1个墙垛子后面 。但那些墙垛子都很小,肯定藏不住老三 。她一路找已往,一直找到校门了,还没看见老三,她知道他真的只是路过这搭了 。那一天,她总是心不在焉,下战书上体育课的时候她又把球打出去了几次,还帮别人翻了几次墙,但都没看见老三 。放学后,她回家吃了饭,到班上的包干区去看看几堆烧在那里的枯树叶烧完了没有 。今天该他们组扫除包干区,地上有太多的落叶,一般遇到这种情况,各人就把落叶扫成堆,点火烧化,待会儿只把灰烬扔到乐瑟堆就行了,不用一大筐一大筐地把落叶运到乐瑟堆去 。组里的人懒得在那里等着烧落叶,就叫静秋吃完饭了再来做最后扫除 。静秋看看火已灭了,就把灰烬装到1个畚箕里,准备拿到乐瑟堆去倒掉 。她刚直起腰,就认出篮球类场地上几个打篮球的人当中有1个是老三 。他脱了军大衣,只穿着他那闻名的白衬衫和一件毛背心,正跟几个学生打得热气腾腾 。她一惊,手里的乐瑟都差点泼出去了,他没走?还是办完事又归来了?她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看他打球,觉得他的姿式真是太漂亮了 。他跳投的时候,黑黑的头发随着向上一抛,球落进球网了,头发也乖乖地落回原位了 。她怕他发现她在看他,就赶紧拿着乐瑟跑掉了 。她倒了乐瑟,把畚箕放回教室,锁了教室门,也不回家,就坐在操场另一真个凹凸杠上,远远地看他打球 。总共才4个人,在打半场 。老三已把毛背心也脱了,只穿了件白衬衣,袖管挽得高高的,很精神、很洒脱的样子 。她帮他们计数,看谁投进的球多,最后发现老三投进的至多 。考虑到他是穿着皮鞋的,她对他的仰慕之情真是犹如滔滔江水再加之滚滚河水了,真恨不得他就住在篮球类场地,从早到晚打球给她看 。天渐渐黑了,打球的人散了,有人收了球,边拍边往体育组办公室走去,大概是去还球 。静秋严要地看着老三,不知道他要去哪儿,她好想叫他一声,跟他说几句话,但她不敢,她想他可能是在附近啥子地方办差,下班了某事干,就像学校附近厂矿的那些工人同样,到学校找人打打球混时间 。然后她看见他向她住的那边走去了,她知道他一定是去水管那里洗手去的 。她跟在后面,离得远远的 。果然,他跟那几个打球的都走到水管那里,他等别人把手洗了,离开了,才把大衣啥子的搭在水管旁边的一棵Y字型的老桃树上,走到水管边去洗手 。她差点叫出了声,那桃树上时常有一些粘粘糊糊的桃树胶的,把稳弄在他服装上 。她看见他洗了手,从挂包里摸出1个毛巾,洗了一把脸,甚或拉起衬衣擦了擦上身,看得她直抖,替他冷 。他洗完了,穿回毛背心,走到靠食堂那一壁,她知道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她的家门 。他站了一会儿,就拿起大衣披在肩上,提了挂包,向她家后面那个方向走去 。她家后面不远方就是个茅厕 。说实话,她起根没想过他也上茅厕的,刚起头她连他食饭都不敢看,就觉得他应该是张画,不吃炊人烟 。后来好了一点,觉得他食饭是件正常事了,但她也就进步到那个程度,觉得他就应该是只进不出的 。现在瞅见他往茅厕走,想到他居然也上茅厕,她觉得太尴尬了,不敢再跟踪他,飞快地逃回家去了 。回到家,她又忍不住走到窗户,想看看他从茅厕出来后会到哪儿去 。她家的地势比窗后的路高,差不多要高出1个人那么多 。她站在窗子边,暗暗往外望,没看见他从茅厕出来 。但她往下一望,就一眼看见老三站在不远方,脸对着她家的窗子,她吓得蹲了下去,头碰在窗前的课桌上,撞得“咚”的一响 。她母亲问:“怎么回事?” 她连连摆手叫母亲别措辞,然后她就那样半蹲着,走到屋子前边她住的那边去了,才敢站起身 。她知道他眼力再好也不成能瞅见隔墙后面的她,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怕啥子 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又暗暗走到窗户,往外看了一眼,他已不在那里了 。她不知道他刚才看见她没有,如果看见了,那他就知道她其其实偷偷看他了 。她站在窗边看着窗外那条路,看了好一会儿,也没看见他,她想他可能走了 。天都黑了,他会去哪儿呢? 她回到自己住的那半间房,边织毛衣边痴心妄想 。过了一会儿,有人在敲门,她以为是老三,心中严要地思索该怎么对母亲撒谎 。但等她开了门,却看见是学校钟书记的小儿子,叫钟诚,手里提着个烧水的壶,看样子是到外面水管来打水的 。钟诚对她说:“我姐姐叫你去一下 。” 钟诚的姐姐叫钟萍,静秋平时跟她也有些接触,但不算走得很密的朋友 。她不知道钟萍现在叫她去干啥子,就问:“你姐找我干啥子?” “我不知道,她就叫我来叫你 。快去吧 。” 静秋跟在钟诚后面往外走,走到水管那里,她正想往右拐,去钟诚家去,但钟诚指着左面说:“那边有个人在找你 。” 静秋一下子意识到是老三在找她,一定是他看见钟诚来水管打水,就叫钟诚去叫她出来的 。她对钟诚说:“谢谢你了,你去打水吧,别对人讲 。” “知道 。” 静秋走到老三跟前,问:“你……你……找我?” 他小声说:“想跟你说几句话,利便不利便?不利便就拉到 。” 她正想措辞,就看见有人从茅厕那边过来了,她怕人看见她在跟1个男的措辞,会传得满城风雨,拔腿就往学校后门方向走 。她走了一段,弓下腰,装作系鞋带,往后望了一下,看见老三远远地随着 。她站起身,又往前走,他仍然远远地随着 。她走出了校门,他也跟出了校门 。他俩沿着学校院墙根儿走了一会儿,来到早上她捡球的地方,他跟了上来,想措辞,她截断他,说:“这搭人都认识我,我们到远点的地方再说吧 。”说完,就又走起来 。他远远地随着她,她一直沿着学校院墙走,从学校后面绕到学校前门,来到那条小河前 。他又想跟上来措辞,又被她打断了 。她就一直走,一直走,走到渡口了,才想起自己没带钱,她等了他一下,他很乖地跟上来,买了两张船票,给了她一张 。两人一前一后地上了船 。一直到了对岸下了船,又沿着河岸走了一段,静秋才站下等他 。他快步追了上来,笑着说:“像是在演影戏《跟踪追击》 。” 静秋解释说:“河那边的人都认识我,过了这道河,就没人认识我了 。” 他会心地一笑,随着她接续往前走,问:“我们要走哪儿去?别走太远了,把稳你母亲找你 。” 静秋说:“我知道前边江边有个亭子,亭子里有板凳可以坐一下 。你不是说有话说吗?我们去那里措辞 。” 两个人到了那个亭子,里面空无一人,大概是天太冷了,没有谁会跑出来喝四面风 。亭子就是几根柱子扛着个顶子,四面穿风,静秋找个柱子边的座位坐了,但愿柱子几多可以挡一点风 。老三在柱子另一边儿的凳子上坐下,他问:“你食饭了没有?我还没吃晚餐 。” 静秋急了,劝他:“那你去那边餐馆吃点东西吧,我坐这搭等你 。” 他不去 。她怕他饿,又劝他,他说:“我们一路去吧,你说了这搭没人认识你,就当陪我去吃吧 。你不去,我也不去 。” 静秋只好跟他一路去 。他们找了一家荒僻冷清的餐馆,是家“小面馆子”,就是不卖饭,只卖面食的那种 。老三问她想吃啥子,她坚持说她啥子也不吃,说你再问我就跑掉了 。老三吓得不敢问了,叫她在桌子边坐着等,他自己去列队 。静秋已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上过餐馆了 。还是很小的时候,她跟爸爸母亲一路上过餐馆,多半是吃早餐,无非是小笼包、油条、豆浆、油饼之类的 。但这些在“文革”当中也被拿出来批斗过了,说他们家是资产阶层生活方式 。爸爸在“文革”初期就被揪出来了,减了工资,后来又被赶旋里下去了,以是她应该有七八年没上过餐馆了 。平时早饭就是在家炒剩饭吃,或在学校食堂买馒头 。后来因为差粮,就总是买那种尾面馒头吃 。尾面是面粉厂打面粉的时候其余的边角废料,黑糊糊的,很粗很难吃,但因为不要粮票,静秋家早饭多半吃那个 。老三买了不少东西,分几次端到桌子边来 。他递给她一双筷子,说:“你无论如何随便吃点吧,否则我也不吃了 。” 他劝了几遍,她不动筷子,他也不动,她只好拿起筷子吃点 。刚好老三买的东西是她钟头候最喜欢吃的,就像他钻到她心中去看过了同样 。他买了“大油饼”,外面像油饼同样是炸得黄黄的,但里面有糯米的心子,加了葱,香气扑鼻 。他买了几个肉小笼包,蒸得白白的,还在冒热气,让人很有食欲 。他还买了两碗面,汤上边有葱花和香油星子,闻着就很好吃 。她同样吃了一点,不善意思吃太多 。不知道为啥子,静秋每次吃老三买的东西的时候,心中就很不安,仿佛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,背着家人在外面大吃大喝同样 。她想如果她也有很多钱,能把一家人带到餐馆里,大手大脚地用钱,想吃啥子就点啥子,那就好了 。但她没这些钱,现在家里不仅缺钱,还缺粮 。为了填饱肚子,她母亲请人弄到一种票,可以买碎米,就是小得像沙粒的米,是打米厂打坏掉的米,以前都是卖给农民喂猪的,现在不知怎么拿出来卖给人吃,一斤粮票可以买四斤,差粮的人就买碎米吃 。碎米很难吃,一嚼就满嘴乱跑 。最糟的是碎米很不洁净,同化着很多碎石子和谷头目,每次淘米就得花半钟头、一钟头的,因为要把碎米泡在1个脸盆里,再用1个小碗,每次舀一点米,和着水,慢慢荡,慢慢荡,先把浮在水面的谷头目荡掉,再把米荡进另1个脸盆里,舀一碗水,荡很多下,只能荡一点米出来,然后再舀水,再荡,直到碗里只其余石子了就倒掉 。静秋总是亲自淘米,因为母亲很忙,妹妹又太小,淘不洁净,如果把那些石子、谷头目吃下去,掉到盲肠里去了,会得阑尾炎的;而且大冬季的,手浸在刺骨的冷水里一淘半钟头一钟头,妹妹的手也受不了 。她很吊唁在西村坪的那些日子,食饭不用交粮票,不管有菜没菜,饭总是可以敞开吃的 。吃得差不多了,老三踌躇片刻,小心翼翼地说:“我说个事,你不要生气,行不行?”他见她颔首了,就从衣袋里拿出一些粮票,“我——有些粮票,多出来的,我用不着,你要么嫌弃,就——拿去用吧 。” 静秋推脱说:“你自己用不着,寄归去你家里人用吧 。” “这是L省的粮票,我家在A省,寄归去也没用 。你拿着吧,如果你用不着,就随便给谁吧 。” “你怎么会其余恁地多粮票?” “我们队直接从西村坪买粮,底子不用粮票的 。” 她听他这样说,就收下了,说:“那——就谢谢你了 。”她看见他满脸是由衷的感谢,仿佛是她刚给了他很多粮票同样 。吃完饭,静秋跟老三一前一后往亭子那里走 。她想:拿了人家的手软,吃了人家的嘴软,今天又拿了他的,又吃了他的,不是处处都软了? 21 两个人又回到亭子那里坐下,可能刚吃过东西,似乎不觉得冷了 。老三问:“还记得不记得去年的今天?” 她心中一动,他真的是为这个来的 。但他不说她也记得,只淡淡地说:“你说有话跟我说的呢?有啥子话就快说吧,过一会儿渡口要封渡了 。” 他仿佛已把啥子情况都摸清楚了,说:“十点封渡,现在才八点 。”他看了她一会儿,小声问,“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了——我以前那个女朋友的事?” 她更正说:“是你未婚妻 。”这个词其实是太正规了,但在本地口语里,没有1个跟“未婚妻”相应的土语 。如果用“对象”或“女朋友”来代替,又觉得没到火候,不能体现出问题的严重性 。他笑了一下:“好,未婚妻,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了,我们早就……不在一路了 。” “瞎扯,你自己对大嫂说的,你有未婚妻,你还给了照片给她 。” “我对她说我们在一路,是因为她要把长芬介绍给我 。他们一家都对我那么好,我怎么好……直接说不行呢?”他声明说,“但我们两年前就分手了,她婚都结了 。你要么信的话,我可以把她的信给你看 。” “我看她的信干啥子?你不会编一封信出来?”她嘴里说着,手却伸出去了,问他要信 。他摸出一封信给她,她跑到路灯下去看 。路灯很昏暗,不过她仍然可以看出是封分手的信,说老三存心回避她,在外面流落,她等了太久,心已死了,不想再等了,云云 。信写得不错,比静秋瞅见过的那些绝交信写得好多了,不是靠毛主席诗词或语录撑台子,看得出是有文化的,而且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 。静秋看了一下落款,叫“丹娘”,她脱口问道:“丹娘不是个苏联女英雄吗?” “那时的人都兴起这些名字,”他解释说,“她比我大几岁,是在苏联出生的 。” 静秋听说丹娘是在苏联出生的,敬佩得无以言表,而且一下就把她跟那个拿不定主意爱谁、跑去问山楂树的女人接洽起来了 。她自卑地问:“她是不是……好漂亮?长芳和大嫂都说她很漂亮 。” 他笑了一下:“漂亮不漂亮,要看是在谁的眼睛里了 。在我眼睛里,她——没有你漂亮——” 静秋觉得鸡皮疙瘩一冒,这种话也说得出口?一下就把他的形象搞坏了,又从“湿裤”公子变回“纨绔”公子了 。试想,1个正派人会当着别人面说人家漂亮吗?而且他这是不是算得上自由主义了?当面不说,暗地里胡说,开会不说,会后胡说,这不是毛主席批评过的自由主义偏向吗? 静秋知道自己不漂亮,以是知道他在撒谎,必然在哄她 。问题是他这样哄她的目的是啥子?可能转来转去,又回到那个“据有”的问题上来了 。她四面一望,方圆几百米以内1个人都没有 。刚才还在为此地荒僻冷清心喜,现在有点畏惧自己把自己丢到陷阱里来了 。她决心要提高小心,拿了他的也不强手软,吃了他的也不能嘴软 。她把信还给他,反咬一口:“你把她的信给我看,申明你不能替人保守奥秘,谁还敢给你写信?” 他苦笑了一下:“我这也是没辙了,一般来讲,我还是很能替人保守奥秘的,可是……我不给你看,你就不会信赖我,你叫我有啥子办法?” 不知道为啥子,他这样说,令她很舒服,仿佛他在赞颂她的威力同样 。她进一步敲打他:“我早就说了,你这样的人,能对她出尔反尔,就能对……别的人出尔反尔——” 他急了:“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?毛主席还说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呢,我跟她是家长的意思,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。” “现在是新社会,哪儿还有啥子怙恃包办的婚姻?” “我不是说怙恃包办,我们也没有婚姻,只是两边家长要推成这个事 。说了你可能不信赖,所说的干部子弟当中,恰好有很多都是怙恃的意思,即使不是怙恃一句话说了算的,也是怙恃从小注意让他们的子女多跟某些人接触,只跟某些人接触,以是到头来,几多都有点怙恃的因素在其中 。” “你喜欢这样被包办?” “我当然不喜欢 。” “那你为啥子要答应呢?” 他沉默了一阵:“当时的情况比力特殊,关系到我父亲的政治前途——甚或生命,这事三言两语也讲不清,不过请你信赖,这事早就已往了,我跟她真的只是——可谓是——政治联姻吧 。以是我一一直等到在勘探队,很少归去 。” 静秋摇摇头:“你这个人好狠的心哪,你要么就跟她好说好散,要么就跟她结婚,你怎么可以这样……拖着人家呢?” “我是要好说好散,可是她不肯,两边家长也不赞成,”他低着头,嗫嚅地说,“反正这事已做了,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,可是你要信赖我,我……对你是真心的,我不会对你出尔反尔的——” 她觉得他说这些话,完全不像他借给她的那些小说里的人物的语言,反而像长林这样的人会说的话,她有点失望,怎么不是像书里那样的呢?虽然那些书都是毒草,应该批判,但读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。她想她必然中了那些书的毒了,总觉得爱情就应该是那样的 。她问:“这就是你今天要跟我说的话?好了,你说了,我可以归去了吧?” 他抬头看着她,仿佛被她这种冷冷的神情惊呆了同样,半牛人说:“你……你还是不信赖我?” “我信赖你啥子?我就知道出尔反尔的人不值得信任 。” 他叹口气:“现在才知道为啥子书里总是写‘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’ 。以前觉得这样写很庸俗,浮夸,现在才知道这是真正的感觉 。不知道怎么才气让你信赖,真的想把心掏出来 。” “心掏出来都没人信赖 。毛主席说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,好,我不打死,可是毛主席仿佛还说过:从1个人的已往,就能够瞅见他的现在;从1个人的现在,就能够瞅见他的未来 。” 他仿佛被她的话打哑了,她看着他,有点得意 。他看着她,说不出话,好久才低声叫道:“静秋,静秋,你可能还没有爱过,以是你不信赖这世上有永恒的爱情 。等你爱上谁了,你就知道世上有那么1个人,你宁肯死,也不会对她出尔反尔的 。” 她被他两声“静秋”叫得一颤,浑身倡议抖来 。她不知道他为啥子叫她“静秋”,而不叫她“小秋”或别的啥子,她也不知道他为啥子要连叫两声,但他的语调和他的表情使她觉得心头发颤,觉得他仿佛是1个被冤枉判了死刑的人,在等候青天大老爷救他一命同样 。不知道为啥子,她就觉得自己信赖他了,信赖他不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了 。她说不出话,但越抖越厉害,深深呼吸了几次都不能止住抖 。他脱下军大衣,给她披上,说:“你冷吧?那我们往回走吧,不要把你冻坏了 。” 她不肯走,躲在他的军大衣下接续发抖,好一会儿,她才抖抖地说:“你……也冷吧?你……你把大……衣穿了吧……” “我不冷 。”他就穿着个衬衣和毛背心,坐在离她两三尺远的地方,看她穿着棉袄,还在军大衣底下发抖 。她又抖了一阵,小声说:“你如果冷的话,也……躲到大衣底下来吧 。” 他迟疑着,仿佛在揣摩她是不是在考验他同样,他定定地看了她好一会儿,才移到她身边,掀起大衣的一边儿,盖住自己半边身子 。两个人像同披一件雨衣同样披着那件军大衣,等于是啥子也没披 。“你还是冷?”他问 。“嗯……嗯……也……不是冷……,还是你……穿大……衣吧,我……我穿了也没用……” 他试探着握住她的手,她没反对,他就加了力,接续握着,仿佛要把她的抖给捏掉同样 。握了一会儿,他见她还在抖,就说:“让我来想个办法——我只是尝尝,你不喜欢就马上告诉我 。”说着,他站起身,把军大衣穿上,站在她眼前,两手拉开两边的衣襟,把她严严实实地裹在里面 。她坐在那里,头只有他肚子那么高,她想现在他看上去一定是像有了毛毛同样,肚子变大了 。她不由得笑了一下,人也不那么抖了 。他垂下头,从大衣缝里看她:“是不是笑我像个孕妇?” 她被他料中,而且他又用了“孕妇”恁地1个“文妥妥”的词,她笑得更厉害了 。他把她拉站起来,两手拉着大衣两边的前襟使劲裹着她,说:“这下就不像孕妇了——”但他自己很快抖了起来,说:“你……你把……抖传给我了……” 她靠在他胸前,又闻到那种让她头晕的气味了 。不知道为啥子,她仿佛很但愿他使劲搂她同样,仿佛她的身体里有些气体,把她的人胀得泡泡的,需要他狠狠挤她一下才气把那些气挤出去,否则就很难受 。她不善意思告诉他这些,也不敢用自己的手搂着他的腰,只把两手放在身体两边,像立正同样站着,往他胸前挤了一点 。他问:“还……还冷?”于是再抱紧一些,她感觉舒服多了,就闭上眼睛,躲在他胸前的大衣里,好想就这样睡已往,永恒也不要醒来 。他抖了一会儿,小声叫道:“静秋,静秋,我以为……再也不能这样了,我以为那次把你吓怕了 。我现在两手不空,你拧我一下,让我看看是不是在做梦……” 她扬起脸,问:“拧哪儿?” 他笑:“随便拧哪儿,不过现在不用拧了,肯定不是做梦,因为在我梦里,你不是这样措辞的 。” “在你梦里我是怎样措辞的?”她好奇地问 。“我做的梦里,你总是躲我,叫我不要随着你,叫我把手拿开,说你不喜欢我碰你 。你梦见过我没有?” 静秋想了想,说:“也梦见过——”她把那个他揭发她的梦讲给他听 。他仿佛很负伤:“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梦?我肯定不会那样对你的,我不是那样的人——我知道你很担忧,很畏惧,但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。我只想保护你,照顾你,让你幸福,我只做你愿意我做的事 。可是你让我摸不透,以是你要告诉我,你愿意我做啥子 。否则我可能做了啥子你不喜欢的事,而我还不知道 。只要你告诉我了,我啥子都愿意做到,我啥子均可以做到 。” 她好喜欢听他这样说,但她又警告自己:这种话你也信赖?他骗你的啦,这种话谁不会说?她刁难他:“我要你在我毕业之前都不来找我,你也做获得?” “做获得 。” 提到毕业,静秋不成避免地想到毕业后的前景,担忧地说:“我高中读完了,就要下屯子了,我下去了就招不归来了 。” “我信赖你一定会招归来的——”他刚说完这句,就解释说,“我不是说如果你招不归来我就不爱你了,我只是有信心你一定会招归来的 。万一招不归来的话,也没涉及系,我可以到你到农村的地方去 。” 其实这个对静秋来讲还真不是个问题,因为在她看来,两个人相爱,其实不需要在一路的 。关键是两个人相爱,离得远近儿都没啥子区别,可能离得越远,越能证实两人是真心相爱 。“我不要你到我到农村的地方去,我就要你等我 。” “好,我等你 。” 她又软土深掘:“我不到二十五岁不会谈朋友的,你等得来?” “等得来,只要你让我等,只要我等你不会让你不开心,我等一辈子都行——” 她扑哧一笑:“等一辈子?比及了,人也进寿材了,那你为啥子要恁地等呢?” “就为了让你信赖我会等你一辈子的,让你信赖世上是有永恒的爱情的——”他又低声叫道,“静秋,静秋,其实你也能一生一世爱1个人的,你只是不信赖别人会那样爱你,你以为自己一无是处,其实你……你很伶俐,很漂亮,很善良,很可爱……很……我肯定不是熬头个爱上你的人,也不是最后1个,不过我信赖我是最爱你的那1个 。” 22 静秋就像1个滴酒不沾的人俄然学喝酒同样,喝熬头口的时候,很不习气,呛得流泪,觉得那味道又辣又热,烧咽喉,不明白那些酒鬼怎么会喝得那么津津有味 。但多喝几次,就习气于那股辣味了 。慢慢地,就品出点味道来了 。可能再往下,就要上瘾了 。老三刚才那些让她冒鸡皮疙瘩的话现在变得柔和动听了 。她仰起脸,痴迷地望着他,听他讲他熬头次见到她时的感觉,讲他见不到她时的魂不守舍,讲他怎样坐在学校附近的1个脚手架上看她练球,讲他步行几十里去大嫂外家拿核桃,讲他用五毛钱“贿赂”那个来水管打水的小男孩去叫她出来 。她仿佛听上了瘾,越听越想听 。他讲完一段,她就问:“还有呢?再讲1个 。” 他就笑一笑,像他那次在山上讲故事同样,说:“好,再讲1个 。”于是他就再讲一段 。讲了一会儿,他俄然问:“那你呢?你也讲1个我听听 。” 她马上避而不谈了 。不知道为啥子,她仍然觉得不能让他知道她喜欢他,仿佛一告诉他,她就“失脚”了同样 。如果他喜欢她,是因为她也喜欢他,那就不稀奇了 。只有在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他的情况下,他还是喜欢她,那样的喜欢就是真喜欢了 。她矜持地说:“我哪像你有那么多闲工夫?我又要上学又要打球 。” 他垂下头,专注地看着她,她心中一慌,心想他肯定见得她在撒谎了 。她把脸扭到一边儿,避免跟他视线相对 。她听他低声说:“想1个人,爱1个人,其实不是件丑事 。不用因为爱1个人而感到羞愧,每1个人或迟或早都会爱上1个人的,都会得相思病的……” 他的声音有种令人信服的力量,她觉得自己差不多要向他认可啥子了 。但她俄然想起《西纪行》里的1个情节,孙悟空跟1个妖怪交锋,那个妖怪有个小瓶子,如果妖怪叫你名字你答应了,你就会被那个小瓶子吸进去,化成水 。她不知怎么的,就觉得老三手里就拿着那样1个小瓶子,只要她说出她喜欢他了,就会被吸进他那个小瓶子里去,再也出不来了 。她硬着嘴说:“我没觉得……是丑事,可是我现在还小,还在读书,我不统考虑这些事的……” “有时候不是自己要考虑,而是心中头不成避免地会想到 。我也不想打搅你进修,我也不想天天睡不好觉,可是仿佛控制不住同样……”他看了她一会儿,痛下决心,“你安心读书吧,我等你毕业了再来找你,好不好?” 她俄然觉得毕业是个多么特别长的事呀,还有好几个月,他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她这几个月都见不到他了?她想声明说她不是这个意思,想告诉他“只要么会被人发现,你还是可以来看我的” 。但她觉得他看她的眼神仿佛是早已揣摩出了她的心思,存心这样说了让她发急,让她自己暴露自己同样 。她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:“毕业之后的事,还是比及毕业之后再说吧,现在恁地早说了也没用,谁知道我们那时是啥子情况?” “不管那时是啥子情况,反正你毕业之后我会来找你 。不过,在你毕业之前,如果你有啥子需要我做的,一定告诉我,好不好?” 她见他下了恁地坚定的决心,而且下得恁地快,她心中很失落,看来他见不见她均可以,其实不像他刚才说的那样对她朝思暮想 。她生气地说:“我有啥子需要你做的?我需要你做的就是不要来找我 。” 他很尴尬地笑了一下,没措辞 。过了好一会儿,才低声说:“静秋,静秋,你这样熬煎我的时候,心中是不是很开心?如果是,那我就没啥子话说了,只要你开心就好 。可是如果你……你自己心中也很难受,那你为啥子要这样熬煎我呢?” 她心中一惊,他真是侦察兵啊,连她心中想啥子他均可以侦察出来,不知道他那小瓶子有多厉害,会不会把侦察出来的也吸进去了?她克制不住地又抖起来,坚持说:“我不知道你在瞎扯些啥子 。” 他搂紧她,小声安慰说:“别生气,别生气,我没说啥子,都是胡说的 。你不喜欢我——就不喜欢我吧,我喜欢你就行了 。”说着,就用他的脸在她头顶上轻轻蹭来蹭去 。他那样蹭她,使她觉得头顶发烧,而且一直从头顶向她的脸和脖子放射已往,搞得她脸上很发烧,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啦,就对无辜人发怒于他:“你干啥子呀?在别人头上蹭来蹭去的,你把别人头发都弄乱了,别人待会儿怎么归去?” 他笑了一下,学她的口气说:“我来帮别人封建把头发弄好吧 。” 她嗔他:“你会弄啥子头发?别把我头发弄得像鸡窝同样 。”她挣脱他一些,打散辫子,五爪金龙地梳理起来 。他歪着个头看她,说:“你……披着头发……真好看 。” 她龇牙咧嘴:“你措辞太恶心了!” “我只是脚踏实地,以前没人说过你很美吗?肯定有很多人说过吧?” “你胡说,我不听了,你再说我就跑掉了 。” 他马上说:“好,我不说了 。不太长得漂亮不是啥子坏事,别人告诉你这一点,也没有啥子不好的用心,你不用害羞,更不用发别人脾气——”他见她准备编辫子了,就说,“先别扎辫子,就这样披着,让我看一看——” 他的眼神充满了恳求,她有点被打动了,不自发地停下了手,让他看 。他看着看着,俄然呼吸短促地说:“我……可不成以……吻一下你的脸,我保证不碰别的地方 。” 她觉得他的表情仿佛很痛苦同样,有点像他周围的空气不够他呼吸似的,她俄然有点畏惧,怕如果她不赞成,他会死掉 。她小心地送过一边儿的脸,说:“你保证了的啊——” 他不答话,只搂紧了她,把他的嘴唇放在她脸上,一点一点地吻,但他没敢超出脸的规模 。他的胡子有点锥人,呼吸也热热的,使她觉得又冲动又畏惧 。他的嘴唇几次走到她嘴唇边了,她以为他要像前次那样了,她一阵慌乱,不知道待会儿要么要像前次那样紧咬牙关,但他把嘴唇移走了,一场虚惊 。他就那样在她脸上亲了又亲,她有点担忧,怕待会儿半边脸都被他的胡子锥红了,届时一边儿唱红脸,一边儿唱白脸,怎么回家去?她小心地挣脱了,边梳辫子边娇嗔他:“你……怎么不了没了的?” “会有很永劫间见不到你嘛——” 她笑起来:“那你就多亲一些,存哪儿慢慢用?” “能存着就好了——”他仿佛有点心神不定、手脚无措同样,胸脯起伏着,盯着她看 。她好奇地问:“怎么啦?我辫子扎歪了?” “噢,没有,”他说,“挺好的,不早了,我送你归去吧,说不定你母亲处处找你 。” 一听这话,静秋才想起刚才出来时没跟母亲打招呼,她慌了,忙问:“几点了?” “快九点半了 。” 她急了:“那快点走吧,河里封渡了我就回不去了 。”两个人急仓促地往渡口赶,她担忧地问,“你待会儿到哪儿去困觉?” “随便找个地方就行,旅馆啊、招待会儿啊都行 。” 她想到河对岸是郊区,没啥子旅馆、招待所之类的,就劝他:“那你别送我过河了,省得待会儿封渡了,你就回不到这边来了,那边没旅馆的 。” “某事 。” “那你待会儿不要跟我太紧了,我怕河那边的人看见了 。” “我知道,我只远远地随着,看你进了校门就走——”他从挂包里拿出一本书,递给她,“把稳,里面夹着一封信,我怕没机会跟你措辞,就写下来了 。” 她接过书,拿出夹着的信,塞进衣袋放好 。一回到家,妹妹就埋怨说:“姐,你跑哪儿去了?母亲处处找你,从魏红他们家归来的时候,踩到阴沟里去了……” 静秋见母亲的腿擦破了一大块,涂了些红药水儿,红红的一大片,很吓人 。母亲小声问:“恁地晚,你跑哪儿去了?” “去……钟萍那里——” 妹妹说:“妈叫我到钟萍那里找过了,钟萍说你底子没去她那里 。” 静秋有点生气:“你们恁地处处找干啥子?我1个朋友从西村坪来看我,我出去一下,你们搞得恁地调兵遣将,别人还以为我——” 母亲说:“我没有调兵遣将,钟诚跑来叫你的时候,我听见了 。后来看你恁地晚还没归来,就叫你妹妹去他家看一下 。在魏红家我只说是找他们借东西的——母亲没有恁地傻,不会对人说自己的女儿恁地晚还没归来的 。”母亲叹口气说,“但你也太大胆了,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,也不告诉我你几点归来 。现在外面乱得很,你1个女人子,如果遇到蛆虫了,这辈子就完了 。” 静秋低着头不吭声,知道今天犯大纰缪了,幸好母亲只是擦伤了腿,如果出了大事,她真的要悔怨死了 。母亲问:“你那个——西村坪的朋友是——男的还是女的?” “女的 。” “你们两个女人子恁地晚跑哪儿去了?” “就在河边站了会儿——” 妹妹说:“我跟母亲去过河边了,你不在那里 。” 静秋不敢措辞了 。母亲叹口气说:“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伶俐很懂事的孩子,你怎么会做恁地傻气的事呢?有些男的,最爱打你们这种小丫头的主意了,几句好听的话,一两件花服装就能哄到手 。你如果被这样的人骗了,你一生来就有完了 。你现在还在读书,如果跟啥子蛆虫混在一路,学校开除你,你这辈子怎么做人——”母亲见静秋低着头不措辞,就问她,“是那个长林吗?” “不是 。” “那是谁?” “是个勘探队的人,我跟他没啥子,他今天到这搭办差,他说他有些粮票用不了,就叫我拿来用 。”静秋说着,就把粮票拿出来,想将功抵销罪过 。母亲一看那些粮票,更生气了:“这是男人惯用的伎俩,用小恩小惠拉拢你,让你吃了他的嘴软,拿了他的手软——” “他不是这样的人,他只是想……帮我 。” “他不是这样的人?那他明知你还是个学生,为啥子还要把你叫出去,玩到半夜才归来?他如果真的是想帮你,不会光明正大地上我们家来?搞得恁地偷偷摸摸的,哪1个好人会这样做?”母亲伤心地叹气,“整天就是怕你上钩,怕你一失脚成千古恨,跟你说了几多回,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?” 母亲对妹妹说:“你到前边去一下,我跟你姐姐说几句话 。”妹妹到前边去了,母亲小声问:“他——对你做过啥子没有?” “做啥子?” 母亲迟疑了一会儿:“他——抱过你没有?亲过你没有?他——” 静秋很心慌,完了,抱过亲过必然恶劣的事,否则母亲怎么担忧这个?她的心形容心跳乱跳,硬着头皮撒谎说:“没有 。” 母亲如释重担,交接说:“没有就好,以后再不要跟他交往了,他肯定不是个好人,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蛊惑还在读书的女人 。如果他再来纠缠你,你告诉我,我写信告到他们勘探队去 。” 23 那天晚上,静秋好久都失眠,她不知道老三归去的时候,渡口封渡了没有 。如果封渡了,他就过不了河了 。她住的此地叫江心岛,四面都是水,一条大江从上游流来,到了江心岛西端就分成两股,一股很宽很大的,从岛的南面流过,本地人叫做“大河” 。另一股小点的,从岛的北面流过,本地人叫它“小河”,就是学校门前那条河 。这两股水在江心岛东端会合,又还原为一条大江,向东流去 。一到炎天,四面的水都涨上来,可以涨得跟地面平齐,但起根没有淹过江心岛 。听老人们说江心岛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,以是永恒不会被淹没 。大河的对岸是江南,但却不是诗里面赞美的那个江南,而是比力贫穷的屯子 。小河的对岸是K市城市地区,江心岛属于K市,算是城市郊区,隔河渡水的,不大利便 。岛上有几个工场,有1个农业社的菜蔬队,有几个中小学,有些餐馆、菜市啥子的,但没有旅馆 。静秋担忧老三今晚过不了小河,只能呆在江心岛上,就会露宿陌头 。恁地冷的天,他会不会冻死?就算他过了河,也不见得能住上旅馆,听说住旅馆要有办差证实才行,不知道他有没有证实 。她满脑子都是老三紧裹大衣、缩着脖子、在街上流浪的画面,后来还酿成老三坐在那个亭子里过夜,冻成了冰棍,第二天早上才被几个扫公路的人发现的画面 。如果不是怕把母亲急病了,她现在就要跑出去看看老三到底过了河没有,到底找到旅馆没有 。她想如果他今晚冻死了,那他就是为她死的了,她一定要跟随他去 。想到死,她其实不畏惧,因为那样一来,他们俩就永恒在一路了,她再也不用担忧他出尔反尔了,再也不用担忧他爱上别人了,他就永恒都是爱她的了 。如果真是那样,她要叫人把他俩埋在那棵山楂树下 。不过埋在那树下仿佛不太可能,因为他俩不是抗日英雄,不是为群众好处而死的,只是一男一女为了相会,1个冻死,1个自杀 。按毛主席的说法,他们的死是轻于鸿毛,而不是重于泰岳的,怎么够资格埋在那棵树下呢?那些埋在树下的抗日英雄肯定要有意见了 。问题是她还有母亲和妹妹要照顾,如果她死了,他们怎么办?那只好先把妹妹养大了,把母亲安放好了,再去死 。但她肯定会跟他去的,因为他是为她死的 。静秋在外间床上展转反侧,她听见母亲在里屋床上展转反侧 。她知道母亲一定在为今天的事着急 。她信赖母亲不会擅自跑到老三队上去告他,母亲没有恁地傻,恁地黑心,因为这完全是损人而倒霉己的事,这样一来,不光害苦了老三,也把她贴进去了 。但她可以想象获得,从今以后,母亲就要更加为她操心了,几分钟不见她就会以为她又跑去会那个“坏男人”了 。她想告诉母亲,其实你不用为我担忧,他这半年不会来了的,他已说了,他要比及我毕业了才会来找我 。说不定到了那一天,他早就把我忘记了 。他有的是女人喜欢,他嘴巴又恁地甜,我都被他哄成这样,如果他要哄别的女人,那还不是唾手可得? 她忍不住又把今晚的情景追念了很多遍,而且老是围绕着他抱她亲她这两个中间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。究竟是她这个人思惟很不健康,还是因为她母亲对这两件事谈虎色变?这两件事把母亲都吓成那样,一定是十恶不赦了,而她刚好都做了,怎么办呢?到底被他抱了亲了会有啥子害处?她有点想不明白 。前次他也抱了她,亲了她,仿佛没怎么样呀 。但若没害处,那母亲为啥子又那么怕呢?母亲是过来人,难道还不知道啥子可怕啥子不成怕吗? 老三今晚仿佛有点冲动,他那算不算“兽性大发”?“兽性”究竟是个啥子性?兽跟人不同的地方不就是野兽是会吃人的吗?他又没吃她,只温情眽眽地吻吻她罢了,没觉得有啥子跟野兽相同的呀 。一直到了第二天,她才有机会把老三的信拿出来读 。那星期该她锁教室门,她就比及别人都走了,才坐在教室的1个死角里,摸出那封信拆开了看 。老三的信写得很好,可谓是温情、热情加深情 。他写到他自己的那些思念的时候,她看得很感动,很舒服 。但他把她也写进去了,而且他写她的那个格调有点不合她的胃口 。如果他只写他怎么爱她,怎么想她,不把她写得像个共谋,她会很欣赏他的信 。但他还写了“我们”怎么怎么样,这就犯了她的忌讳了 。她也收到过一些情信,大大都是她同学写的 。不管写信人文字程度凹凸,她最反感的就是写信人自作多情地猜测她是对他有意思的 。记得有1个男学生,也算作文写得不错的,但那人真叫厚颜无耻,每次写信都仿佛她已把她的心交给他了同样 。她不理他,他说那是她喜欢他的表现,因为她对他的态度不同凡响;如果她跟他说了一句话,那更不得了,他马上就要夸大其词地写到信里去,当作她喜欢他的证据 。预计你就是对他吐口吐沫,他都会认为那是你喜欢他的证据:为啥子她只对我吐,不对别人吐呢?这不是申明她跟我关系纷歧般吗? 通常情况下,她还是很尊重很感谢那些给她写情信的人的,一般不会让人家下不来台 。但对这个厚颜无耻的同学她真的是烦透了 。他不仅写信给她,还对人讲,说他在跟静秋“玩朋友”,搞得别人拿他们两个起哄,连她母亲都有一半信赖了,说:“如果你起根没答应过他啥子,他怎么会那样说、那样写呢?” 后来静秋忍无可忍,拿着那个家伙的信跑到他家去告了一状,他才收敛了一些 。她不明白老三恁地伶俐的人,为啥子看不出她不愿意他把她热情的一壁写在信里呢?她愿意他把她写成1个冷冰冰的人,而他则苦苦地爱她,最后——注意,是一直到了最后,只管她不知道这个最后是啥子时候——她才给他1个爱的表示 。她觉得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的,就是从熬头章就起头追,一直追到最后一章女人才松口 。她本来当时就要把老三的信撕掉扔到茅厕里去的,但她想到这封信有可能是老三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了,她又不忍毁掉了 。她趁母亲出去家访的机会,把那封信也缝在棉袄里了 。她能感觉到母亲对她管得比以前紧了,连她去魏红家都要问几遍,仿佛怕她又跟前次同样,说是去钟萍家,结果却跟1个勘探队的人跑出去了 。她想想就觉得不公允,她哥哥也是很早就有了女朋友,但母亲起根没有像这样防贼同样防着她哥哥,反而很热肠地帮助招待哥哥的女朋友 。每次哥哥的女朋友要来,母亲都想方设法买点肉,做点佳肴招待她,还要提前一天把床上的垫单、被单搜罗一空,大洗特洗,结果有好几次都累得尿血了 。母亲总是说:“我们这种人家,要钱没钱,要权没权,身分又不好,除了一份热情,我们还拿得出啥子?”
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,仅作参考!温馨提示:如遇健康、疾病相关的问题,请您及时就医或请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!
「四川龙网」www.sichuanlong.com小编还为您精选了以下内容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:- [转载]单车运动的好处
- [转载]怎样选择合适的健身球
- [转载]明星们掀起一场模仿玄彬的“亮金属片运动服”热潮
- 转载——健身教练职业发展报告
- 转载 四加行和上师瑜伽3
- [转载]运动礼仪 打保龄球须知的礼仪
- [转载]中国足球,别折腾!
- [转载]最新韩版男生头像晋江最具长大性运动休闲品牌20强
- 2011年中考体育仰卧起坐最热足球遇冷
- 十个值得推荐最消耗脂肪的减肥运动